陳舊的社會觀念底下,性別定型嚴重,女生學拳或被看作是花拳繡腿,貽笑大方,或者純粹為減肥塑身,剛陽不足,打不出個氣候。
但這種想法要徹底被顛覆了,因為澳門出了一個土生土長、本土拳館訓練出來的女拳手,從本地打到亞洲,再從亞洲打到世界,屢屢刷新澳門的最高記錄。
譚思朗學拳即將屆滿十年,精通踢拳和泰拳。十七歲入拳館的她,並不算太早接觸該領域,但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從零開始,只消兩年,她就登上了比賽擂台爭高下。

聽到比賽就燃起一團火
思朗坦言十七歲的她無心向學,整天「掛住出去玩」,後來更由日校轉為夜校,四出留連無所事事,她形容「成班人坐公園都唔返屋企」。這個階段的她,過得一天是一天,談不了什麼目標,至於跑到拳館,也不過有朋友報名,就柴娃娃地跟,最多也只是找個機會多做運動。誰知,戴上拳套,一試就喜歡上,之後放工會自發到拳館報到,跟師兄們大伙人一起操練。
當時女性拳手非常罕見,思朗作為拳館的兩名女學徒之一,頻繁且持之以恆的操練似乎也給了教練們一些靈感。「有日師父跟我說想組女子隊,叫我有時間多點回去,將來試組織一些女拳手參加比賽。」

人生第一個比賽是香港員警會拳擊邀請賽,對手是員警和消防員,工作所需勤於體能操練,亦精於搏擊,相信上場並不好應付。豈料思朗初露頭角,即見鋒芒,贏了個52公斤級女子組冠軍。
「一開始好緊張,但目標很清晰,就是要贏。」思朗稱這樣的心態「有好有唔好」,但不諱言贏了真的好開心,雖然知道始終心態尚未夠成熟,但至少有信心繼續打下去。

「小時候好喜歡玩環山跑比賽、單車比賽,什麼運動都玩,甚至曾在學界攞奬。好鐘意比賽的感覺,也很喜歡攞奬,一有比賽我就報名。」思朗說得坦率而誠懇,即使「喜歡贏」的自我評價從她口中說出,也不會讓人聽著有尖銳感和不適感。
但其實「喜歡贏」又怎麼了? 埋藏起力爭上游的志氣,選擇表現得「人蓄無害」,這些人總是毫無鋒芒。
報章上見到的思朗總是捧著奬牌,但正如套餐似的捆綁式消費,想要贏,總是無法迴避輸。當然,戰場上沒有人想輸,思朗亦是如此。直至,在擂台上遇到一位來自塔吉克斯坦的對手,讓她改變了。
2016年的韓國武術大師賽,當時二人第一次對陣,實力相差無幾,經歷一場勢均力敵,最後思朗還是不敵,塔吉克斯坦的對手險勝。
然而一場敗局並不是最終局,17年的亞洲踢拳錦標賽,二人再次擂台相遇。「我是一個很不服輸的人。」全靠這種「不服輸」,讓她經歷了一年的技術攀升,加上落敗之後有刻意研究這位選手的拳法,鑽研制勝方法,再一次同台,思朗更有信心技術取勝。

只是,「不服輸」這股衝勁可成,也可敗。「又遇上於是更加想贏,不停想不停想,就算賽前的夜晚也想到睡不著。感覺自己跌回二零一二年第一次打比賽時的思想狀態,只想著要贏。」
結果又輸了,屈居亞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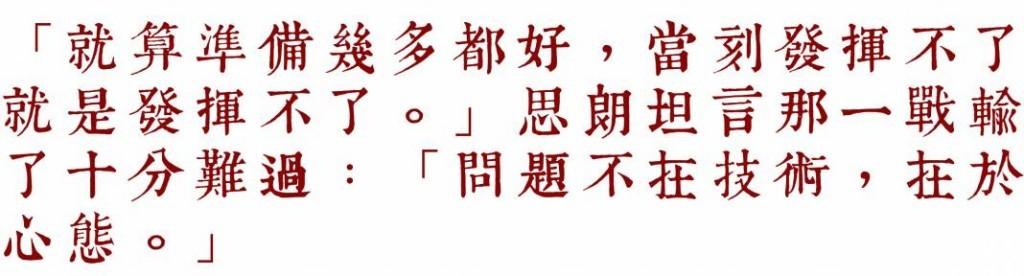
一贏再贏全因一敗再敗
成為同一個對手的手下敗將,是她對自己要求的失落。然而,縱觀整個比賽,她仍是成績斐然,載譽而歸。兩個賽事奪得的銀牌,已經是女子踢拳亞洲賽事當中,澳門所得的最高奬項。思朗開始被鎂光燈照亮,亦多了人對澳門的拳藝運動另眼相看。
而思朗最大的收獲,來自接著的一封電郵。「收到電郵立刻到世運會網站查詢,發現果然有我的名字。」她自言喜出望外,原來取得的兩面銀牌,為她帶來了第10屆世界運動會的參賽資格,在兩個亞洲代表席位中佔上一席。
能夠打上世界賽擂台的,澳門前無來者。

提到那場世界賽,思朗回味起來仍十分起勁,她形容「經驗好正」、「超開心」、「好深刻」、「好難忘」。那場世界賽是一個驚喜,因為她早不知道自己已備晉身資格,加上首次離開亞洲遠赴波蘭出賽,接觸前所未有的大型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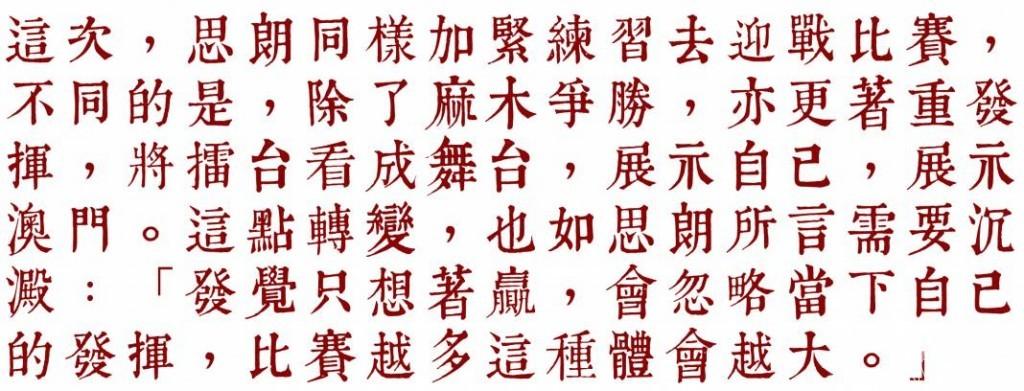
於是,同一個對手,同一套戰術,在世運會的擂台上,思朗最終將來自塔吉克斯坦的對手擊倒,這個曾一次又一次將她屈居項背的宿敵。打到第三次,終於成功發揮。

跟塔吉克斯坦對手的多番對戰,使她突破了瓶頸以及心理上的界限,意識到要更多地集中在自己身上。「最初輸了反而得到更多,所以很多謝這位對手,給了我人生一個好重要的成長經歷。」
擂台上誰不想爭第一? 只是想嬴,就要有輸的準備;而只當輸得起,才能贏得起。

一個人勝利因為不止一個人
亞洲賽贏過兩面銀牌,最終一八年在澳門主場,為東道主爭得一面金牌,這是澳門第一面,亦是思朗在亞洲賽的第一面,意義重大。

「最後對泰國,對手很強,泰拳始終是他們的國粹,我打得好辛苦,只一路死撐。」而最尾反壓局面取勝,當然不只靠技術和心態。


洶湧的打氣聲中當然少不了家人的,由於之前都是往外地比賽,家人從來沒有在現場看過。而這場比賽,自小把思朗帶大的婆婆終於可以到場支持。

這位家人,對她意義尤其重大。除了因為感情要好,婆婆亦是一位十分通明的人,總是二話不說地支持她的決定,即使思朗想做的事,跟「成就」的主流定義背道而馳。「無論是由中學時日校轉夜校然後找工作,學拳然後打比賽,婆婆會問為什麼,但最後總是支持。」於是思朗在家人的支持下選擇了彈性的工作,而不追逐朝九晚五的穩定,讓自己可以投放多點時間訓練。

至於女生打拳,雖然婆婆「覺得行行出狀元」,卻始終有其危險性,見著都會擔心和心痛。「她覺得是女生,有時打腫了眼睛,受傷之類不好。她總是先教訓我,然後就烚一隻雞蛋幫我去瘀。」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尤其是一個與別不同的「好動兒」,家人的愛與痛惜確實內心矛盾。
未上戰場先餓一場
回來一副面青眼腫的模樣,婆婆見著心痛至極。但叫婆婆直捶心肝的,遠不止於此。
搏擊比賽按選手重量分級,拳手為了爭得進入特定的量級賽事,都要經歷一個痛苦且嚴格的快速減磅過程,在戰略上這幾乎無可避免。
雖然未及職業拳手般,進入瘋狂甚至威脅生命的極限減重,但正如思朗所講,減磅「令到成個人謝謝哋」,不比密集鍛鍊輕鬆,過程需要極大的意志磨練。
賽前訓練密集,運動量大幅提高,但拳手為了減磅,反其道重訓之後嚴格控制飲食。這當然不可能完全禁食,而且消耗肌肉作為減重代價,也會影響訓練和比賽表現,所以也要科學減重,達到「又要減又要維持力量」,思朗說「食就一定要食,但整個月也是清茶淡飯。」減重要減少吸收,可以吃的份量和種類也不多,所以免不了有餓肚皮的時候,尤其夜晚經過重度訓練,總想狼吞虎嚥一番,卻在計算營養後發現只能咬一個蘋果解饞充肌;減重期間更不能應朋友邀約外出食飯,思朗笑說﹕「出到去望著別人吃太殘忍,所以乾脆不去。」



「減磅最辛苦是要減水,口乾也只可以濕一下口。」減水是拳手普遍採取的一個快速減磅手段。運動量大令流汗增多,卻因為水被身體吸收後佔有重量,所以就連水,都不能盡情地傾倒入口,甚至要刻意脫水,來讓體重下跌,順利過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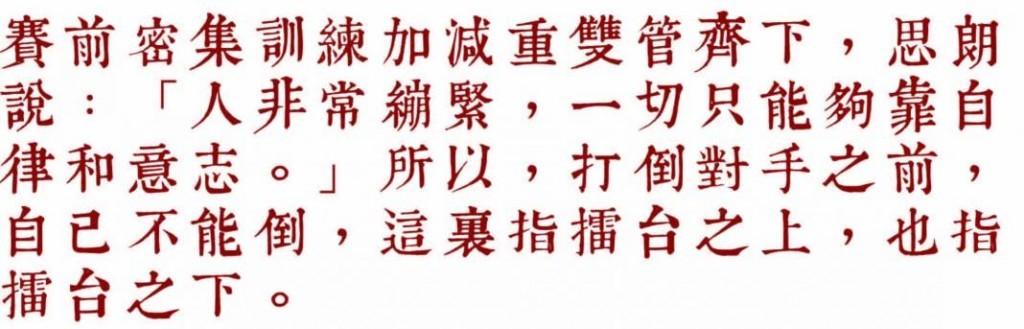
未上戰場先夢一場
在擂台打出的精彩一拳,可能過去已經在沙包前揮動了成千上萬遍。腳踏實地練拳不用說當然必需,但原來光攤著不動,然後想入非非做幾場白日夢,也是一項關鍵訓練。


「走入會場,全場滿座,一陣叫囂聲此起彼落;昂首闊步地跨步上台,向裁判和觀眾敬禮,再回到旁邊的座位;立即開始扭頭擺臂放鬆全身,戴牙膠,戴頭盔;回到台中央,準備,flight!」備戰時,每個星期要做幾次模擬比賽的冥想訓練。
體力訓練耗盡每一吋肌肉的力量之後,閉起雙目,平躺地上,攤開四肢,放鬆,慢吸,慢呼。漸漸地,意識進入平靜而集中的狀態,隨著教練的聲音引導,將比賽的每個環節由始至終排演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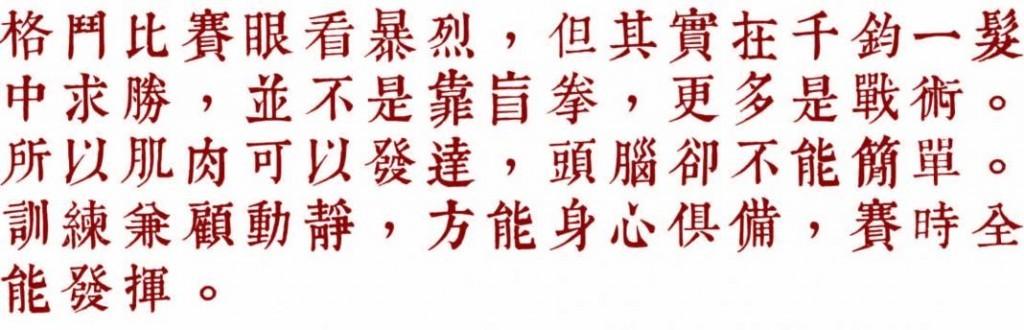
格鬥比賽眼看暴烈,但其實在千鈞一髮中求勝,並不是靠盲拳,更多是戰術。所以肌肉可以發達,頭腦卻不能簡單。訓練兼顧動靜,方能身心俱備,賽時全能發揮。
冥想也要肆無忌憚地幻想,可以不設實際,可以天馬行空,自設各種場景,把所有可能發生的意外自編自導自演一回。

萬一出場前一刻發現頭盔載不上。。。
在對手主場的比賽,萬一他的支持聲比你大,甚至有人給你喝倒采。。。
萬一上一場突然完賽,兩分鐘後就輪到你上場,而你卻連熱身都未做完。。。
冥想就是要訓練出清醒冷靜的心理狀態,腦袋裡預先準備好各種各樣場景的應對辦法,調節心境,到臨場果真如此,也能胸有成竹,進退有據。
未上戰場先捱打一場
出戰前大約兩個星期,就進入一個瘋狂訓練的備戰階段,朝七晚九,全日各種體能和技術訓練,幾乎從床上一睜開眼,身體就開始猛烈運動,至到筋疲力盡,就攤回床上明天待續。

拳賽是雙人格鬥型運動,精彩在於對戰的層出不窮,所以要應付可能的千變萬化,訓練不會只對沙包出拳,還要跟拳館師兄弟高手過招。
為了迫出水平,師傅安排的對練確實嚴厲,甚至誇張地開個玩笑,可以說儼然一場「欺負式的圍攻」。教練安排十來個師兄弟跟思朗車輪式不停對打,三分鐘一輪,休息三十秒,換下一位師兄弟上陣,如是者十多輪,仿如闖十八銅人陣。

說欺負,因為男女礙於先天體格差異,本來就實力有別,男女對戰幾乎不會在拳擊比賽出現;這樣的訓練安排,一來因為拳館裡面幾乎都是男拳手,二來男女對戰難度更高,當思朗回復女子對戰的時候,更能駕馭。
說圍攻,因為雖則還是一個一個應付,但每位師兄弟都是當晚首次對陣,狀態必然最佳,個個精神奕奕,出拳力度又大又狠,而已經打到第N回的思朗,相比之下體力已經耗減,氣喘吁吁。
這樣的狀態,吃拳哪能避免? 「每一晚也想著,唉,一會回去拳館又要被人打了。」當然師兄弟控制力度,不會將思朗打至受傷,但痛感少不了。
然而,最大的傷害,反而不是痛感,而是吃拳的挫敗感。「對練的時候會有壓力,不停反問自己﹕為何連這拳也避不了? 為何我的拳速那麼慢? 有時卡在瓶頸,或者老是做不到心目中的要求,就會忟憎,忟自己,試過有一兩次練到喊。」
亂拳不及致命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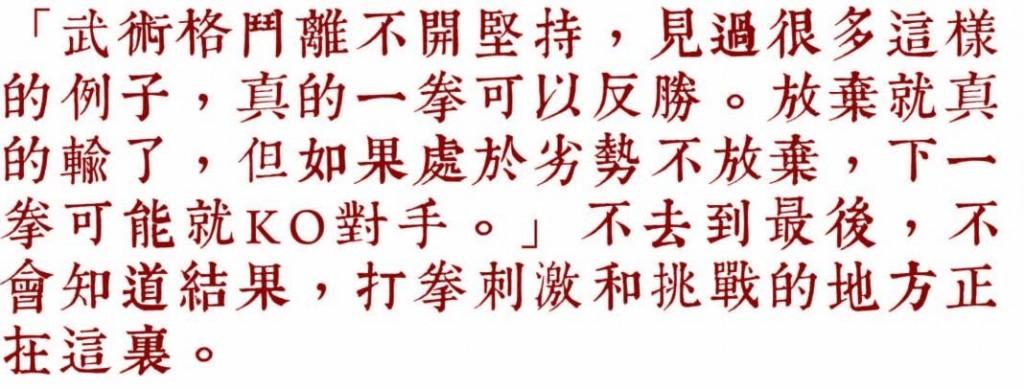
堅持不同死撐,都是將時間延伸,但前者更講策略,不作無謂的消耗,這是一種沉住氣的修煉。「再冷靜的人,上到台都會變得比較衝,一來想贏,二來控制不了自己,於是捶呀捶呀。」思朗回看自己以前和近期的比賽片段,都見有明顯的分別,「冷靜是時間和經驗沉澱之後的收穫。」
她說經驗少的時候不會理會,什麼拳也出,但打拳不是「打爛仔交」,要發揮技術,見招拆招。「現在上場會留意對手招式,量度對手出的拳可延伸到什麼位置,對手如果手長要如何應對,近身打又使出什麼策略,如何製造距離方便閃避……要有好多好多想法在腦海裡純熟應用。」
一次成功可以靠運氣,一直成功就必需靠實力。所以,還是別奢望亂拳能夠打死老師傅。


打到一定打
運動員對於退疫問題總是糾結。思朗在一八年完成幾場大比賽之後,也不停有這方面的思考。「想過要不要見好就收,但每打完一場比賽,雖然都話想停,到最後還是繼續打。」
今年遇上疫情,本來正準備出戰的幾場比賽都取消了。天算不如人算,有時想打,也不一定有機會。大環境增加了不確定性,內心反而減少了不確定性。再回想退疫問題,思朗認為退役不在年紀,而是看心態﹕「不想界限自己,打到一定打。」
有別於職業賽,思朗過往打的拳賽主要是晉級制,賽前一晚抽籤,方知道對手是誰。問到較喜歡哪種賽制,她說﹕「不知道對手會較好,光鬥臨場發揮。之前打過武林群英會,好早就知道要跟國家隊前選手對戰,反而壓力大。」
知己,不求知彼;專注自己發揮,全力以赴,至於外在不可控的,也就隨他不可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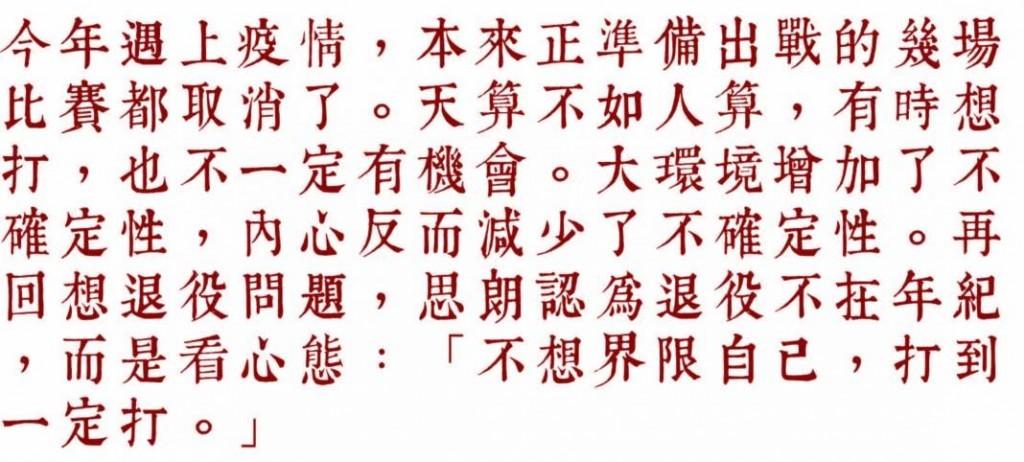
格鬥運動的選手跨上擂台,如果雙方都一副志在參與的優悠,這場拳賽不會精彩。
滿腔鬥志的思朗總不諱言,她喜歡贏。
如果「輸」不該被貼上負面標籤,那「贏」又應該嗎? 只是在平常遵奉謙恭內儉的世界,連這一點欲望都變得難以啟齒。
有想贏的衝勁,也有贏得到的自信,沒有不妥,只是危險。一旦拿捏不稳,容易給人感覺意氣風發,好勇鬧狠。但思朗不然,廿七歲,談吐穩重,思路清淅;對談中,忍不住讚揚她比同齡人都要成熟。她坦誠解釋,這或許跟自己過去年少反叛,不好好讀書,然後很早就出來工作有關。每個受訪者都希望展示自己最亮麗的一面,隱惡揚善。鮮有如思朗,能夠主動重提不算風光的過往。
贏得起亦輸得起,都是戰績的一部分,沒有什麼需要迴避或修飾。果然,成功的運動員看待輸贏,都總有套特別帥氣的風範。
但輸得起,並不等同就此認輸。思朗提到,今年九月,她要重回學堂。過去用了一年時間惡補中學內容,以應付大學入學試,最終得償所願考上了體育系。
是的,她想贏,她總是想贏,不管在擂台之上,還是在人生當中。在人人自居佛系以求自保的時代,這少數敢亮起來的鋒芒,尤其真誠。

採訪:哈皮因
撰文:哈皮因
攝影:Tim @ Tim’s photography
設計:Sam Lok

《ZA誌》(zamag.net) 創立於2012年11月,志在集結一班澳門創作人士從他們眼中介紹澳門鮮為人知的一面及發表屬於澳門人創作的文章或感想。十年以來,《ZA誌》仝人堅持多元共融的創刊理念,並不斷嘗試新的主題和視角,以澳門出發,讓澳門人多一個途徑深入了解身處的城市,也讓世界認識澳門獨特的一面!

